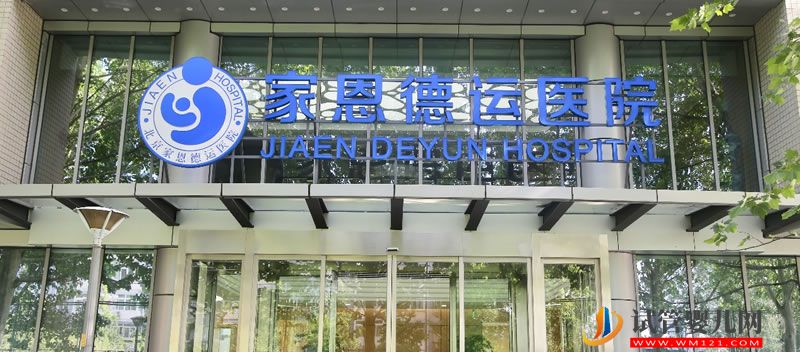iPSC誘導多能干細胞技術:十年進展
由iPSC領域開創者Yamanaka等人在2017年發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的綜述,總結了誘導多能干細胞技術十年以來的進展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technology: a decade of progress |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摘要
自十年前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技術問世以來,干細胞生物學和再生醫學取得了巨大進展。人類iPSCs已廣泛用于疾病建模、藥物發現和細胞治療開發。新的病理機制已經闡明,來自iPSC篩選的新藥正在研發中,并且首次使用人類iPSC衍生產品的臨床試驗已經啟動。特別是,人類iPSC技術與基因編輯和3D類器官的最新發展相結合,使得基于iPSC的平臺在其應用的各個領域(包括精密醫學)都更加強大。在這篇綜述中,我們討論了與藥物發現和再生醫學特別相關的iPSC技術的應用進展,并考慮了該領域其他的挑戰和新出現的機遇。
背景
2006年,科學和醫學領域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有報告稱通過使用四種轉錄因子的混合物,可以從小鼠體細胞(如成纖維細胞)中生成具有類似于胚胎干細胞(ESCs)的基因表達譜和發育潛力的細胞1。這些細胞被稱為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s),四種因子——OCT4、SOX2、KLF4和MYC——被命名為“Yamanaka 因子”。僅僅 1 年后,兩個研究小組獨立報道了從人類成纖維細胞中生成 iPSCs2,3。
自 2007 年以來迅速發展的人類 iPSC 技術(BOX 1)為干細胞生物學和再生醫學領域以及疾病建模和藥物發現領域開創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新時代。該技術開發后不久,人類 iPSC 被迅速應用于生成人類“培養皿中的疾病”模型,并用于藥物篩選的功效和潛在毒性。鑒于對表型篩選的興趣激增以及人類 iPSC 在疾病建模中與傳統細胞篩選相比的優勢,這種方法現在變得越來越流行。這些優勢包括它們源自人類、易于獲取、可擴展、能夠產生幾乎任何所需的細胞類型、避免與人類 ESC 相關的倫理問題,以及使用患者特異性 iPSC 開發個性化藥物的潛力。此外,基因編輯技術的最新進展——特別是 CRISPR–Cas9 技術——正在快速生成基于基因修飾的人類 iPSC 疾病模型。iPSC 也是新一代更具生理代表性的細胞平臺的關鍵組成部分,該平臺包含 3D 架構和多種細胞類型。
BOX 1 |人類 iPSC 技術的演進
自 2006 年開始,誘導多能干細胞 (iPSC) 技術發展迅速。由于 iPSCs 最初是通過整合病毒載體(例如逆轉錄病毒或慢病毒載體)引入重編程因子而產生的,因此由于轉基因整合到宿主基因組中引起的插入誘變的可能性,這些 iPSCs 的臨床應用受到關注細胞 204.
為了使 iPSC 在臨床上更適用,已經開發了各種非整合方法來規避與逆轉錄病毒和慢病毒轉導介導的重編程因子引入相關的插入誘變和遺傳改變的風險 205。這些非整合方法包括使用游離 DNA 206,207、腺病毒208、仙臺病毒209、PiggyBac 轉座子210、小環211、重組蛋白212、合成修飾的mRNA213、微小RNA214,215 和小分子216進行重編程,盡管小分子方法尚不適用于誘導生成人類iPSC。
在這些方法中,游離型 DNA、合成 mRNA 和仙臺病毒通常用于衍生無整合的 iPSC,因為它們相對簡單和高效185。使用非病毒方法或非整合病毒可以避免基因組插入,從而降低人類 iPSC 用于臨床應用時的相關風險。
iPSC技術也因其在再生醫學中的潛在應用而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第一項評估人類 iPSC 衍生細胞的臨床研究于 2014 年啟動。該研究使用人類 iPSC 衍生的視網膜色素上皮 (RPE) 細胞治療黃斑變性4,據報道該治療可改善患者的視力5。盡管由于在第二名患者的 iPSC 中發現了兩個基因變異,該試驗隨后被擱置,但預計將繼續進行 6。
顯然,人類iPSC技術對人類疾病建模、藥物發現和基于干細胞的治療具有很大的前景,而這種潛力才剛剛開始被實現。在本文中,我們概述了自該技術發現以來的十年中 iPSC 在每個主要應用中的進展。我們提供了關鍵的說明性示例,討論了其限制和解決方法,并強調了出現的新機遇。
基于 iPSC 的疾病建模
識別人類疾病的病理機制對于發現新的治療策略具有關鍵作用。動物模型為人類疾病建模提供了寶貴的工具,能夠識別不同發育階段和體內環境中特定細胞類型的病理機制。此外,在小鼠中,有可能開發基于 iPSC 的體外疾病模型和對應的體內模型。將觀察到的表型與相應的體外和體內小鼠模型進行比較,可以更好地了解基于體外人類 iPSC 模型的強度和局限性。
然而,實質性的物種差異可能會阻止在最常用的動物模型(例如小鼠)中重現完整的人類疾病表型。例如,盡管已經為阿爾茨海默病創建了許多轉基因小鼠模型,但沒有一個模型能夠捕捉到人類疾病病理學的整個譜系,包括大量的神經元損失 7、8。這種疾病重演的缺乏可能是由于小鼠和人類神經細胞之間的基本物種差異。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人類疾病建模平臺來補充使用動物模型進行生物醫學研究的研究。
使用原代患者來源的細胞建立疾病模型有助于研究人類疾病的病因學,并為這些疾病制定治療策略。然而,缺乏來自患者的可擴展的原代細胞來源是一個關鍵的限制,特別是一些難以獲得的細胞,如腦細胞和心臟細胞。因此,人類iPSCs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因為原則上人類疾病(特別是那些有明確遺傳原因的疾病)可以很容易地使用來自不同患者的容易獲得的細胞類型(如皮膚成纖維細胞和血細胞)來建立iPSCs模型。由于其固有的自我更新特性和分化為體內幾乎任何細胞類型的潛力,患者特有的iPSCs可以提供大量與疾病相關的細胞和以前無法獲得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細胞,如神經元和心肌細胞。此外,由于 iPSC 可以來自相關患者本身,它們可以實現個性化的疾病建模,這將成為精準醫學的核心部分。
人類 ESC 和 iPSC 都已用于模擬人類遺傳疾病。早期的模型是使用 ESC 開發的,但隨著人類 iPSC 技術的出現,因為它們的可用性和沒有使用人類 ESC 相關的潛在倫理問題,人類 iPSC 已成為首選。人類 iPSC 與人類 ESC 高度相似。這兩種類型的細胞都表達人類多能因子和 ESC 表面標志物,并表現出分化成三個胚層的發育潛力2,3。體細胞的殘余表觀遺傳記憶可能發生在 iPSCs10-12 中,這可能會影響這些細胞的分化潛能。盡管在 iPSCs10-12 中已經報道了親代細胞的表觀遺傳記憶的持久性,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在使用人類 ESCs 和 iPSCs 的疾病建模中已經報道了類似的表型,這支持了使用源自患者的 iPSCs 進行疾病建模的有效性。
使用人類 iPSC 進行疾病建模的過程始于獲得含有致病突變(或多個突變)的 iPSC(圖 1)。然后這些細胞分化成與疾病相關的細胞類型。所得細胞用于揭示疾病病因和鑒定病理機制。在基于 iPSC 的疾病建模的早期研究中,來自未受疾病影響的個體的 iPSC 被用作患者來源的 iPSC 的對照。然而,與其他細胞類似,iPSC 表現出譜系間變異,這使數據解釋變得復雜,因為必須將譜系變異與真正的疾病相關表型區分開來。
圖1|基于人類IPSC的疾病建模示意圖。建立和使用基于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的疾病模型通常包括以下步驟。首先,iPSCs來自患者個體,并使用CRIPSR-Cas9等基因編輯技術創建同基因型對照。然后,將iPSCs分化為特定的細胞類型,如神經細胞,并對生成的細胞進行研究,以確定疾病的特定表型。在分子水平上研究這些表型可以識別新的病理機制,為藥物發現和個性化藥物提供機會。
快速發展的基因組編輯技術現在能夠以特定位點的方式將基因改變引入 iPSC,包括糾正患者來源iPSC中引起疾病的基因突變,以及將特定突變引入非疾病影響的野生型 iPSC。這些方法能夠生成以引入突變為唯一變量的基因匹配的同基因型iPSC系,確保能可靠地識別真正的病理學原因,同時避免與可能的譜系間變異導致的遺傳背景或附帶現象的任何差異混淆。在對散發性或多基因疾病進行建模時,同基因型 iPSC 的控制將特別重要,因為其表型差異很小14。
可編程位點特異性核酸酶的開發,包括鋅指核酸酶 (ZFN)15,16、轉錄激活因子樣效應核酸酶 (TALEN)17-19 和 CRISPR-Cas9 系統20-23(表 1),顯著改善了基因通過在基因修飾位點誘導 DNA 雙鏈斷裂來提高人類 ESC 和 iPSC 的編輯效率。尤其是 CRISPR-Cas9 技術因其設計簡單且易于使用而備受關注,并在人類 ESC 和 iPSC 的基因編輯中得到廣泛應用。這種基因編輯技術使研究人員能夠將致病突變引入野生型 iPSC,并消除患者 iPSC 中的此類突變,從而為基于 iPSC 的疾病建模創建同基因型對照(圖 1)。
然而,在使用CRISPR-CAS9技術的應用中,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可能產生偏離目標的效果。然而,盡管CRISPR-Cas9在癌細胞系24中描述了相對較高水平的非靶標基因修改,但最近來自多個實驗室使用全基因組測序(WGS)的報告表明,在正常人類細胞中,包括人的iPSCs和ESCs25-29,非靶標基因修改是罕見的。使用從原始iPSCs和相應的基因編輯iPSCs中分離的基因組DNA的WGS,結合全面的生物信息學分析25,27-29,對于檢測脫靶效應(如單核苷酸變體(SNV)和插入或缺失(INDELs))是有用的,特別是對于將用于臨床應用的細胞。目前,WGS價格昂貴,但預計隨著技術的發展,成本將會下降。檢測脫靶效應的替代方法包括外顯子組測序30和靶向深度測序29。對于靶向深度測序,人們可以使用Cas-OFFinder31來搜索與人類基因組中的靶外位點不同的潛在的靶外位點,Cas-OFFinder31是一種用于識別非靶標位點的算法,包括非靶標SNV或INDELs。
基因編輯工具也在不斷改進和完善,這可能有助于解決脫靶效應問題。最初的CRISPR-Cas9技術通過使用單個引導RNA指導的野生型Cas9核酸酶誘導DNA雙鏈斷裂來編輯基因組位點。由成對的引導RNA指導的Cas9的尼克酶(nickase)版本(D10A突變體)和具有增強特異性的工程Cas9核酸酶變體(ESpCas9)現在越來越多地被用于基因組編輯32-34,因為兩者都顯示出大大減少了脫靶效應,同時保持了嚴格的靶標切割34,35。此外,催化死亡的Cas9(dCas9)與轉錄激活因子或抑制因子融合可用于調節內源基因(所謂的CRISPRi或CRISPRa)的轉錄,或通過與熒光蛋白32-34、36融合來調節基因組位點的轉錄。對CRISPR-CAS9系統的修改還能夠以精確的單等位基因或雙等位基因的方式高效地顯式引入DNA序列變化37。堿基編輯方面的一項最新進展利用了CRISPR-Cas9和胞苷脫氨酶的融合,使胞苷能夠直接轉化為尿苷,而不需要DNA雙鏈斷裂38。這一新方法提高了基因編輯效率,并將進一步促進人類ESCs和iPSCs的基因編輯。
基于iPSC的疾病模型被廣泛用于研究由單基因突變引起的具有早期發病的特征的疾病(單基因疾病)39,40。這種方法非常適合于此類疾病,因為iPSCs可以很容易地從患者身上分離出來,并分化為與疾病相關的細胞,如神經元。此外,鑒于iPSCs41分化的細胞相對不成熟,更有信心的是,iPSCs分化的細胞表型為早發與晚發的疾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型,對于這些疾病,細胞老化可能在疾病病理學中很重要。例如,從患者來源的iPSCs分化出的神經元被用來模擬脊髓性肌萎縮癥(SMA),這是一種由存活運動神經元1(SMN1)39突變引起的早發性疾病。SMN1基因的突變會導致運動神經元的退化和隨后的肌肉萎縮。1型SMA患者通常在出生后6個月出現癥狀,病情進展迅速,到2歲時會致命42。在最初的基于IPSC的疾病模型研究39中,從1型SMA患者的成纖維細胞中獲得的IPSC被分化為一種與疾病相關的細胞類型,運動神經元。從患者來源的iPSCs分化出的運動神經元與來自未受影響的對照組的運動神經元相比,存活率降低。此外,用丙戊酸和妥布霉素(兩種已知可誘導SMN1表達的化合物)處理患者來源的iPSCs后,SMN1蛋白和含有SMN1蛋白的“GEM”水平增加(參考文獻。39)。這項研究提供了患者來源的iPSCs可以用來模擬早發性遺傳性疾病并作為潛在的藥物篩選平臺的原則證據。
對發病較晚的疾病進行建模更具挑戰性,因為從人類iPSCs分化而來的細胞通常表現出類似胎兒的特性。然而,誘導細胞老化已被用來幫助成功地模擬遲發性疾病43-46。誘導從人iPSCs分化而來的細胞衰老的一種方法是用細胞應激源處理這些細胞:例如,使用以線粒體功能或蛋白質降解通路為靶點的MG-132和吡咯菌酯等化合物。另一種誘導細胞衰老的方法是異位表達導致過早衰老的基因產物,如progerin。然而,細胞應激源或progerin的表達是否能通過與正常衰老相似的機制誘導細胞衰老仍有待確定。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細胞成熟和老化可能是不同的事件41,48。目前尚不清楚細胞老化誘導劑是否可以促進細胞成熟和衰老,而不是在未成熟細胞中引發細胞衰老48。或者,直接重編程方法,包括將人成纖維細胞直接轉化為其他特定血統的細胞,如神經元,不會消除細胞老化標記49。事實上,來自老化成纖維細胞的神經元通過直接重新編程維持細胞年齡50歲,因此為研究與年齡相關的疾病提供了一種替代的細胞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在促進細胞成熟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例如通過使用改進的培養液配方51或使用神經元-星形膠質細胞共培養系統52、53。
iPSCs還提供了一種研究散發性(sporadic )疾病(其原因尚未在患者的家族病史或基因突變中確定)的新方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許多疾病的大多數患者都有散發性疾病。例如,在阿爾茨海默病中,95%的患者屬于散發性類別。有趣的是,對來自散發性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IPSC來源的神經細胞的分析發現,幾個零星病例表現出與由特定基因突變引起的家族性阿爾茨海默病相同的表型54。這一發現表明,使用ipscs對散發性疾病進行重新分類的可能性。然而,使用iPSCs模擬散發性疾病通常比模擬單基因疾病更困難,因為這類疾病的表型變化通常被認為是由多個小遺傳風險變異結合環境因素引起的。盡管來自散發性疾病患者的iPSCs可能包含與疾病相關的風險變量,但因為遺傳和表觀遺傳背景的譜系差異,使用iPSCs來模擬此類疾病是復雜的。這種變異對于模擬散發性疾病更有問題,因為散發性疾病iPSC來源的細胞的表型預計比那些來自單基因疾病的iPSC來源的表型更細微。
因此,基于人類iPSC的散發性疾病模型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產生僅在相關風險變量14上不同的成對同基因型細胞系。使用CRISPR-Cas9技術,產生以特定疾病相關遺傳風險變異為唯一變量的受基因控制的同基因型iPSC系的能力可以創建一個受控良好的系統。最近,這種方法被用來產生不同于帕金森病相關風險變量的同基因型iPSC系,與等位基因特異性分析相結合,能夠有力地剖析這種遺傳風險變量55。這一實驗策略可用于研究與其他疾病相關的遺傳風險因素。
到目前為止,已經使用源自iPSC的單一疾病相關細胞類型研究了許多疾病。例如,iPSC 衍生的神經元已被用于模擬阿爾茨海默病 54、56-68(表 2)和帕金森病 43-45、55、69-84(表3)。然而,可能需要不止一種細胞類型來有效地模擬某些疾病。事實上,類似的努力已經致力于使用患者 iPSC 衍生的神經元 85-87 和神經祖細胞 88-92 來模擬精神分裂癥。為了更好地概括疾病表型,可能還需要一種以上細胞類型的共培養來研究不同細胞類型的相互作用。例如,星形膠質細胞-神經元共培養物已被用于模擬肌萎縮側索硬化( ALS )93–96。這種共培養系統使研究疾病病理學的非細胞自主方面成為可能,否則,單細胞類型(如神經元)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此外,這些研究有助于確定星形膠質細胞是導致肌萎縮側索硬化癥運動神經元變性的關鍵細胞成分,并為使用患者iPSC衍生星形膠質細胞93-96進行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的藥物篩選提供了平臺。
使用3D類器官可以更好地模擬不同細胞類型之間的相互作用。使用小鼠和人類的組織干細胞和多能干細胞97,已經為包括大腦、視網膜、腸道、腎臟、肝臟、肺和胃在內的多個器官生成了類器官。由于與內源性細胞組織和器官結構相似,人類iPSC衍生的類器官已被開發用于各種應用,并且特別有用,因為它們能夠在模擬人類生理和發育的細胞環境中研究細胞-細胞相互作用。事實上,3D類器官已被用于模擬人體器官發育和疾病,測試治療性化合物和細胞移植98-114(表4)。在類器官中可以按照時空順序生成多種生理相關的細胞類型。此外,由于三維結構中不同細胞類型(如神經元和星形膠質細胞)的相互作用,在類器官中生成的細胞在功能上可能比使用定向分化培養衍生的細胞更成熟。因此,3D類器官有助于在發育相關的時空背景下解剖疾病病理學,并有可能在器官水平而不是單個細胞水平上模擬藥物反應。
雖然3D類器官為基于iPSC的疾病建模提供了非常有前景的工具,但類器官技術存在局限性。一個挑戰是創建一個與傳統2D培養相比效率和可復現性更高的類器官平臺115。最近,具有3D設計的小型旋轉生物反應器的應用使前腦類器官的生成具有高重復性110。開發更標準化的類器官培養基,以及更明確的細胞外基質,將進一步促進生成高度可重復的類器官系統,該系統更適用于準確的疾病建模、藥物發現和治療開發116。另一個挑戰是當前類器官系統缺乏血管97。因此,由于缺乏持續的營養供應,類器官的生長和成熟受到限制。旋轉生物反應器和振蕩培養平臺能夠提供更好的營養供應,并促進類器官的生長110,117。此外,與內皮細胞共培養能夠在類器官99中生成血管樣網絡。此外,將體外生成的人類類器官移植到動物宿主的相關部位有助于類器官的血管化和成熟。當研究需要增大尺寸和改善成熟度的類器官時,可以應用這種移植方法。
基于iPSC的藥物發現 療效篩選
許多藥物篩選基于被認為與疾病機制相關的靶點。然而,源于靶向篩選化合物的低成功率導致了對表型篩選的更大興趣118。表型篩選的復興得益于iPSC的發現,原因有很多,包括iPSC生產的可擴展性,這有助于分析開發。此外,iPSC的多能性意味著這些細胞可以分化為多種疾病相關的細胞類型,尤其是那些在難以獲得的細胞,如神經元119。患者衍生的iPSC模型可以在培養皿中重現疾病表型和病理。從患者來源的iPSC分化出的細胞可以呈現分子和細胞表型。如果負責疾病表型的基因已知,則可通過基因編輯方法確認選擇作為藥物篩選讀數的表型是否與疾病真正相關,并可在患者樣本和/或動物模型中進一步驗證120。除了表型篩選外,iPSC還可用于基于靶點的篩選。使用人類iPSC模型進行了許多藥物篩選,并使用表型篩選或基于靶點的篩選確定了潛在候選藥物。
為了大規模獲得高純度的靶細胞,已經建立了使用特定細胞表面標記121,122、細胞特異性啟動子123和microRNAs124的純化和富集技術。在首次報告的基于ipsc的疾病模型的大規模藥物篩選中,我們從來自家族性自主神經功能異常(一種以感覺和自主神經系統神經元變性為特征的單基因早發疾病)患者的iPSCs中篩選和純化了自主神經神經元的神經嵴前體121。該疾病是由IκB激酶復合物相關蛋白(IKBKAP)突變引起的,該突變導致剪接缺陷和產生功能失調性截斷蛋白。藥物篩選使用了6912種化合物,其中一種名為SKF-86466的化合物改善了疾病特異性異常剪接。有趣的是,SKF-86466對非靶細胞(包括誘導多能干細胞、成纖維細胞和淋巴細胞)無效。這些結果說明了基于ips的藥物篩選在探索細胞類型特異性發病機制方面的優勢。
Burkhardt等人125使用來自散發性ALS患者的誘導多能干細胞進行了疾病建模和藥物篩選。作者在這些患者的運動神經元中發現了TAR DNA結合蛋白43 (TDP43)的從頭聚集,因此利用TDP43聚集作為高含量藥物篩選的讀數,以識別降低TDP43聚集的化合物125。該研究團隊還有效地利用了患者衍生的阿爾茨海默病iPSC模型126。作者在一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誘導多能干細胞衍生的皮層神經元條件培養液中發現了一種與疾病相關的蛋白——細胞外tau (eTau),然后生成了一種針對eTau126的治療性抗體。如果沒有人類iPSC模型,這種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就不會被發現。eTau導致神經元過度活躍,增加淀粉樣蛋白-β的產生。使用人類iPSC模型作為識別疾病相關靶點的工具可能是未來藥物開發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Naryshkin等發現,在使用HEK293細胞系進行初步篩選后,患者來源的SMA iPSC模型可用于驗證人類和疾病特異性藥物反應性。這些化合物隨后在患者特異性成纖維細胞和從患者來源的誘導多能干細胞分化的運動神經元中進行了驗證,誘導多能干細胞作為患者特異性和疾病相關的細胞模型127。最后,在小鼠模型中評估選中化合物的體內活性127。該藥物發現方法包括一個患者來源的iPSC模型作為驗證步驟之一,該模型利用了患者iPSC來源的運動神經元的患者特異性和疾病相關特性。
總的來說,基于iPSCs的藥物篩選已被用于評估幾種疾病的1000多種化合物121,125,128129(表5),并已確定了幾種臨床候選藥物126,127,130(表6)。然而,這些研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數周或更長時間)將iPSCs分化為與疾病相關的細胞類型。雖然對于表型篩選來說,這段時間似乎并不長,但較短的分化期更有利于避免細胞質量的變化。因此,正在尋求更快和更穩定的導致更高的成熟度和純度分化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使用直接轉分化產生的細胞進行藥物篩選。直接轉分化迫使目標體細胞(例如,成纖維細胞)表達細胞特異性轉錄因子,并在不經過iPSC狀態49132的情況下將一種體細胞狀態重編程為另一種體細胞狀態。直接轉分化已被用于從不同類型的體細胞(如成纖維細胞)中重新編程心肌細胞、肝細胞、神經細胞或其他類型的體細胞。如上所述,直接轉分化的一個優點是可以產生反映細胞衰老重要方面的真實的人類神經元。然而,這種方法提供的不可再生的細胞來源可能不適用于大規模的藥物篩選。轉錄因子的強制表達也提供了更快速分化患者誘導多能干細胞的潛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強制表達肌源性分化1 (MYOD1),骨骼肌分化的主要調節因子,被用于產生新的頑固性肌肉疾病病理的細胞模型,如Miyoshi myopathy133和duchenne型肌營養不良134。
在使用誘導多能干細胞的病理學研究中,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對照組的性質。對于遺傳性疾病,可以通過建立患者來源的誘導多能干細胞中突變等位基因的基因校正來建立一個對照組。通過比較不同組的iPSCs(健康iPSCs、患者iPSCs和基因校正的患者iPSCs)來驗證藥物篩選119的結果。在散發性疾病中,誘導多能干細胞也是非常寶貴的模型。在這些案例中,由于沒有已知的因果突變,很難確定對照組的性質;然而,可以考慮疾病相關的單核苷酸多態性(SNPs) 65。如下文“展望”部分所述,對于未來的藥物篩選,散發性疾病誘導多能干細胞應有助于調查疾病是否由遺傳因素(如SNPs、體細胞突變、嵌合或表觀遺傳因素)引起。這些發展可能進一步打開使用iPSCs135進行個性化藥物篩選的大門。
疾病特異性誘導多能干細胞的另一個應用是藥物的重新定位,即對已經批準用于特定疾病的現有藥物進行測試,以發現其他疾病的新應用。例如,一個來源于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受體3 (FGFR3)突變的軟骨發育不全患者的人類iPSC模型顯示,患者來源的iPSC不能很好地分化成軟骨組織136。利用該模型,篩選從缺陷軟骨表型中拯救軟骨分化誘導多能干細胞的分子,確定了幾種他汀類藥物,這些藥物已被批準用于心血管疾病。該研究還發現,在fgfr3相關疾病的小鼠模型中,他汀類藥物可以促進縮短肢體的生長。這些結果表明他汀類藥物可能被重新定位為軟骨發育不全的候選藥物136。作為藥物重新定位的另一個例子,抗癲癇藥物ezogabine在運動神經元疾病ALS的iPSC模型中顯示了療效,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137。在這項研究中,作者展示了ezogabine對iPSC模型的影響,該模型來自于超氧化物歧化酶1 (SOD1)基因突變的ALS患者,以及與ALS相關的其他基因(如C9ORF72和FUS)突變的ALS患者。也有研究表明,來自ALS患者的iPSC運動神經元最初表現為超興奮狀態,隨后興奮性下降138。這一發現表明,在ALS的治療中,早期干預使用ezogabine可能是必需的。在不同的患者組中觀察到相似的藥物反應,使藥物反應在不同ALS類型中得到推廣。利用一種疾病的多種遺傳形式衍生的誘導多能干細胞進行藥物發現具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它允許在廣泛的患者人群中測試藥物的反應性。相比之下,同時分析一種藥物在多個小鼠模型中的作用是具有挑戰性的。
毒性篩查
新藥的開發成本巨大。高成本主要是由于失敗,尤其是后期臨床試驗中的失敗,這又部分是由于未預料到的副作用139,140。新候選藥物可能會出現許多無法預料的不良反應,心臟和肝臟毒性尤其值得關注。因此,人們對開發能夠更有效地預測候選藥物引起嚴重副作用的可能性的方法產生了相當大的興趣,從而能夠選擇在后期試驗中由于毒性而不太可能失敗的候選藥物。
QT 間期延長的致死性心律失常占總心臟毒性的 21%141。QT 延長是與人類 ether-a-go-go 相關基因 (hERG; 也稱為 KCNH2) 通道有關的不利影響。心臟安全性測試主要依賴于 hERG 測定,因為阻斷 hERG 電流被認為與稱為尖端扭轉型室性心動過速的致命室性心律失常有關。然而,已經發現 40-60% 的抑制 hERG 通道電流的藥物不會導致 QT 延長 142,143。這些來自 hERG 檢測的假陽性結果可能阻礙了有前景的藥物的開發。已經提出了各種臨床前策略來檢測藥物誘導的電生理心臟毒性,包括使用體外人離子通道測定、基于人的計算機重建和人干細胞衍生的心肌細胞144。最近的努力表明,使用人 iPSC 衍生的心肌細胞的多電極陣列可以為臨床前體外測試 145 提供可靠、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物,可用于評估促心律失常風險 146。
對于肝毒性,廣泛使用肝細胞系或人原代肝細胞。然而,這些模型也有局限性,包括細胞資源、凍融導致的功能喪失和批次間差異。最近,產生了人類 ESC 和 iPSC 衍生的肝細胞,它們表達功能分子,如細胞色素 P450 3A4 (CYP3A4),可以吸收吲哚菁綠 147 并對已知的肝毒性藥物作出反應 148。還報道了功能性 3D 肝器官芽,這可能會導致更好的藥物篩選99。
最后,關于神經系統,目前正在開發一個使用多能干細胞評估藥物不良反應的平臺。為了進行這樣的評估,分析細胞在神經系統中的基因表達變化,例如神經元細胞、間充質干細胞和來自培養皿中的人類 ESC 的血管內皮細胞,已被提出 149.
使用人類 iPSC 產品的臨床應用
基于利用干細胞促進內源性再生過程或替代細胞移植后受損組織的再生醫學的潛力已經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自1998年發現人類esc以來(REF。150)和2007年的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REFS 2,3),干細胞研究界已經繼續確定更適合探索人類細胞治療和內源性修復的來源。圖2總結了開發基于ipsc的細胞治療產品的一般方法。正在進行的13項臨床試驗評估干細胞治療產品,8項用于ESC-, 1項用于ipsc衍生的RPE細胞治療黃斑變性,黃斑變性會導致眼內光敏受體的進行性惡化(見臨床試驗)151。2014年,第一項使用人類iPSC產品的臨床研究開始于移植從患者自己的iPSC衍生的RPE薄片。治療取得了積極的結果,停止了黃斑變性,改善了患者的視力。盡管該試驗后來由于在另一位患者的iPSCs4中觀察到突變而被擱置,但預計將恢復6。此外,最近的一項研究已經證明了將嵌入纖維蛋白支架的人類ESC來源的心臟祖細胞移植到嚴重心力衰竭患者的可行性152。
圖2 |人類ips細胞治療示意圖。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為基礎的細胞療法的發展可以分為六個步驟。首先,從患病患者身上收集體細胞進行培養。第二,病人的體細胞被重新編程為誘導多能干細胞。第三,利用基因組編輯技術或病毒轉導方法對患者來源的誘導多能干細胞進行基因校正。第四,矯正后的誘導多能干細胞分化成所需的細胞類型,作為基因匹配的健康供體細胞。第五,進行細胞鑒定、純度、活性和安全性的質量控制試驗。最后,將基因匹配的健康細胞移植到患者體內進行細胞治療。
然而,在開始常規臨床應用之前,需要解決與基于 iPSC 的治療相關的幾個障礙153。一個問題是 ESC 和 iPSC 的致瘤風險154。由于多能細胞在培養中維持很長時間,它們會積累核型異常和拷貝數變異并失去雜合性155。因此,在臨床使用之前,iPSC 衍生產品需要仔細篩選,以確保缺乏潛在風險的基因改變 155 并嚴格測試以確保其純度、質量和無菌性。對多能性誘導和維持的基礎生物學知識的增加也將有助于降低與人類 iPSC 衍生和維持相關的突變發展和遺傳不穩定性的風險。
盡管從 iPSC 分化的產品未顯示會產生畸胎瘤,但確保最終產品不含可能產生畸胎瘤的未分化細胞至關重要。因此,需要用于將人類 iPSC 區分為具有精確身份和細胞功能的所需細胞類型的改進方案。為此,已鑒定出小分子抑制劑可誘導未分化人類多能干細胞的選擇性和完全細胞死亡,而不影響其分化衍生物156,157。用這些抑制劑處理 iPSC 衍生的細胞產物可能會降低潛在的致瘤性。另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在移植前通過對所需細胞類型的正選擇和使用熒光激活細胞分選對人 ESC 標記物的負選擇來對 iPSC 衍生細胞進行分類。最后,可以在移植前在動物模型中測試致瘤性風險。然而,由于動物相關試驗需要很長時間,這種方法可能不適用于疾病進展迅速的患者。
在人類細胞療法移植之前,遵守良好生產規范是強制性的。一旦細胞被安全輸送,理想情況下應該監測病人潛在腫瘤的發展和免疫系統的激活情況。腫瘤監測的一種方法可能是評估經常伴隨畸胎瘤形成的增強血管生成,其可以使用64Cu標記的環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四聚體(64Cu-DOTA-RGD4)放射性示蹤劑和正電子發射斷層成像159進行檢測。另一種方法可能是聯合使用血清生物標志物(例如癌胚抗原、α-胎蛋白或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和磁共振成像篩查,如最近所述16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法在臨床前階段是非常有用的,特別是如果它們已經是評估終點所需的影像學程序的一部分。它們用于未來人體試驗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仍有待確定。
缺乏誘導免疫耐受的有效方法是人類 ESC 治療的主要障礙。由于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物 (MHC) I 類、MHC II 類和共刺激分子的低表達水平,ESC 曾被認為具有免疫特權。盡管未分化的 ESC 可能具有免疫特權,但它們的分化衍生物可以觸發細胞和體液免疫反應 162。相比之下,自體 iPSC 可能避免同種異體細胞移植所需的終生免疫抑制相關的高成本和嚴重副作用 163。盡管關于未分化 iPSCs 的免疫原性存在一些爭議 164,但最近的研究表明 iPSCs 的分化可能導致免疫原性喪失 165-167。
應用來自個體患者自身 iPSC 或匹配供體的 iPSC 的細胞可能成為精準醫療的基石,并且具有不需要長期免疫抑制來保存移植細胞的重要優勢。事實上,第一個 iPSC 臨床試驗使用的就是來自患者自體 iPSC 的 RPE。使用自體 iPSC 產品進行個性化細胞治療似乎是孤兒疾病的理想選擇,因為不需要大量的細胞庫。然而,對于更常見的疾病,特別是腦血管意外或心肌梗塞等急性常見疾病,考慮到仔細驗證每個細胞系所需的高成本和漫長的時間,自體 iPSC 治療可能不適用于大量患者。由于這些原因,日本 iPSC RPE 試驗的第二階段將使用同種異體產品168。
同種異體 iPSC 方法還可以降低基于 iPSC 的細胞療法的成本。排除高昂的啟動成本,每條 iPSC 生產線的生產成本約為 10,000 至 20,000 美元169。滿足當前良好的生產實踐要求會大大增加這一成本170。生產適合臨床使用的 iPSC 衍生組織產品(例如,用于腦血管意外的 iPSC 神經元細胞的分化、用于心肌梗塞的 iPSC 心肌細胞或用于黃斑退化的 iPSC RPE 細胞)的成本甚至更高,大約為 800,000 美元(參考文獻 169))。為同種異體移植存儲 iPSC 有可能降低成本,因為一種產品可能用于多個患者。為了促進同種異體移植,在臨床前和臨床環境中,需要提高常規免疫抑制方案和用于誘導免疫耐受的新型共刺激阻滯劑方案的有效性 171,172。此外,了解多能干細胞如何與免疫系統相互作用以及為什么它們可能比其他移植細胞更具耐受性,可能會導致識別新的免疫抑制機制和策略163。此外,移植到免疫特權部位可能是克服免疫排斥的一種可能策略。結合基因組編輯策略的最新進展來創建普遍接受的供體細胞可能是另一種替代方法173。
人類 iPSC 平臺與最近開發的基因編輯和 3D 類器官技術的結合可以使人類 iPSC 成為基于干細胞的細胞療法開發的更強大的細胞資源。作為一個原理上的證明,通過基因編輯校正的小鼠 iPSC 已被用于生成造血祖細胞,從而成功治療小鼠模型中的鐮狀細胞性貧血 174。此外,基因校正的人類 iPSC 與 3D 類器官的整合可以使組織能夠作為器官替代療法的來源97。事實上,在原理驗證研究中,人類 iPSC 衍生的肝臟類器官已被證明可以在移植小鼠中成功地產生功能性人類肝臟樣組織。然而,這些方法在人類細胞治療中的應用仍然存在挑戰需要克服。例如,需要解決與基因編輯相關的潛在脫靶效應,以及類器官的局限性,如“基于 iPSC 的疾病建模”部分所述。
展望
誘導多能干細胞的發現為疾病研究提供了一個革命性的新研究平臺。自iPSC第一份研究報告發表以來的10年里,將人類iPSC與其他新技術相結合,在研究疾病機制和潛在治療方法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仍有幾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
iPSC克隆分化效率存在差異,包括來自同一個人的克隆119。在選擇疾病模型研究的對照組時,這些變化是重要的考慮。應用CRISPR-Cas9技術可能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如上所述。目前已有多篇報道表明,iPSC突變的基因校正可以改善分化細胞的疾病表型175 - 178。除了糾正疾病iPSCs中的基因突變,研究人員還成功地將基因突變引入健康iPSCs87,88。然而,CRISPR-Cas9技術與iPSC技術的結合仍然存在一些挑戰,包括CRISPR-Cas9編輯的脫靶效應,對它們進行分析的高成本,以及基因編輯對具有未知致病突變或風險變異的遺傳疾病的有限應用14。然而,這種組合在剖析疾病機制和開發新的細胞療法方面的潛力是很高的。此外,CRISPR-Cas9或基于CRISPR的全基因組基因篩選在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中的應用179,180可以為理解人類iPSC多能性、維持和分化的基本生物學機制開辟一條新的途徑。
與小鼠ESCs和誘導多能干細胞相比,小鼠ESCs和誘導多能干細胞表現為(“naive”)“初始”狀態,是同質的,而人類ESCs和誘導多能干細胞表現為(“primed”)“啟動”狀態,在細胞數量和分化潛能上都是異質的。此外,重編程過程可以產生完全重編程的iPSCs和部分重編程的細胞,它們的分化潛能可能不同183,184。因此,在臨床應用之前,人類誘導多能干細胞需要仔細選擇并充分表征其多能性185。對重編程機制的進一步基礎研究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員開發方法,促進產生標準化的人類iPSC狀態,這將導致減少技術變異,并使識別真正的生物表型。除了影響iPSC分化效率的克隆變異外,疾病建模的另一個障礙是分化細胞成熟過程中的譜系間變異。成熟細胞的獲得需要改善培養條件和利用命運轉換與基因調控119。最近的一項技術,microRNA switch( MicroRNA開關 )124,有望提高iPSCc分化細胞的成熟質量和減少克隆變異。
在傳統的疾病模型研究中,細胞是在二維平面上培養的。然而,具有3D結構的體外模型更接近生理條件,因此可能更適合疾病病理學的研究。利用疾病特異性誘導多能干細胞,誘導幾種3D結構分化的技術已經被報道186 - 191,包括那些類似于皮層、視杯、Rathke’s pouch(拉特克(氏)袋)、小腦和海馬體的結構。利用復雜器官胚芽的動態模式和結構自形成,構建三維結構及其相應的網絡已成為現實。這種策略已經被用于大腦異常和精神疾病的疾病模型。與外胚層組織結構的自組織類似,三維干細胞培養的內胚層組織形成已被開發并應用于胃腸道疾病建模192。來自不同譜系但具有相同遺傳背景的復雜組織之間的生理相互作用,如類器官中的血腦屏障或免疫系統,可以為正常生理和疾病提供新的見解。
盡管目前的3D技術存在一些局限性(198,199),但如“基于iPSCs的疾病建模”部分所述,將疾病特異性iPSCs與3D技術相結合,能夠檢測細胞的時空相互作用,從而揭示生理疾病狀態,從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藥物篩選平臺,并為組織替代治療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然而,將人類干細胞來源的類器官移植到動物體內以產生人類組織或器官可能會在生物醫學倫理學上帶來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新問題,例如移植的人類干細胞與宿主細胞混合并在宿主動物的神經系統和生殖系中發育的可能性。
iPSCs 還提供了一種研究散發性疾病的新方法。在 iPSC 技術發展之前,不可能在細胞模型中分析散發性疾病,但現在有幾項研究已成功模擬散發性神經系統疾病 54、57、65、73、85、108、125、135、201、202。據推測,散發性疾病的病理機制可能與家族性疾病相同。然而,散發性和家族性疾病具有顯著差異,例如發病年齡和嚴重程度以及病理學。
iPSC 模型表明,即使每個個體遺傳風險的影響很小,但綜合影響可能會啟動和加速散發性疾病病理學的發展。此外,即使 SNP 基因分型僅表明一個很小的風險因素,它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使用 iPSC 技術對病理表型進行建模可能會導致對散發性疾病的重新分類。這種重新分類可能對藥物開發產生重要影響。iPSC 建模有可能識別對藥物有反應的患者亞組,包括那些散發性疾病的患者,這應該會提高臨床試驗的質量 119。還預計將結合患者 iPSC 進行醫療記錄和基因組信息的大型隊列分析;因此,iPSC 衍生細胞可以對與疾病相關的單個基因和蛋白質進行更精確的分析。
從疾病iPSC研究中積累信息,結合患者的個性化臨床經驗,將有助于疾病重新定位,其中疾病不是由臨床定義,而是由細胞表型定義。如果對臨床不同疾病的體外 iPSC 模型的細胞表型分析表明表型相同或相似,那么在一種情況下有效的治療可能對其他情況有效。例如,雙相情感障礙的 iPSC 模型識別出過度興奮的神經元細胞 201。在來自 ALS203 患者的 iPSC 衍生的運動神經元中發現了類似的過度興奮。因此,相同的治療劑可能對這些臨床上不同但細胞相似的疾病有效。從各種疾病中積累 iPSC 模型的細胞表型數據可能有助于新的分層和對不同疾病的理解,這也可能導致新的橫截面治療方法。
iPSC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新方法來定義和治療疾病。iPSC代表了一種范式轉變,因為它們現在允許我們直接觀察和治療相關的患者細胞。特別是,他們揭示了疾病表型和基因表達譜之間的新關系,這擴大并加深了我們對患者疾病發展的理解,特別是那些散發性疾病的患者。其他技術的進步,如 CRISPR–Cas9、3D 類器官和 microRNA 開關,將進一步推動基于 iPSC 的疾病建模和治療開發的快速發展。